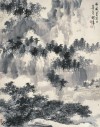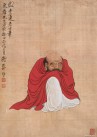书画鉴定大家:谢稚柳
历任上海市文物保护委员会编纂、副主任、上海市博物馆顾问、中国美协理事、上海分会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上海分会副主席、国家文物局全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组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等。著有《敦煌石室记》、《敦煌艺术叙录》、《水墨画》等,编有《唐五代宋元名迹》等。
谢稚柳在书画鉴定上,初与张珩(张葱玉)齐名,世有“北张南谢”之说,张是中国书画鉴定集大成者但英年早逝。后谢稚柳、徐邦达和启功三人齐名,时人多以“艺术鉴定”目谢,以“学术鉴定”目启,以“技术鉴定”目徐。他们在书画鉴定上各有所长,各具特色,形成了三大流派。然鉴定之事非一偏可得全也。
谢稚柳的“艺术鉴定”即从书画艺术的本体,包括意境、格调、笔法、墨法、造型、布局等特征入手进行鉴定,是书画鉴定最直接的路径,是鉴定的筑基功夫。鉴定学中艺术鉴定最难,也最切实。艺术鉴定能解决的问题,一般便无需舍近求远地依靠其它的鉴定方法进行佐证。因此,优秀的书画家,加上深厚的书画史论功底,一般便是当然的鉴定家。古代鉴定家都是书画的行家里手,原因也基于此。正是从这一角度上,传统鉴定的“望气”方法才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谢稚柳最大的长处和贡献正在于此。
在国家文物局古代书画鉴定组成员中,谢稚柳名列首席。他一生的书画鉴定是和他的书画创作互为作用、互为影响的。他从历代大量书画名作中得到创作养料,滋养了自己的创作。反过来,丰富的创作经验又直接对鉴定产生影响。从书画本体出发对书画进行鉴定成为谢氏的主导风格。可以说,谢稚柳的鉴定是艺术鉴定,同时也是鉴定艺术。
谢稚柳先生工诗文,能书法,擅山水、花鸟,亦偶作人物。又与张大千一起对敦煌壁画进行了长期的研究,这使他准确地把握了唐宋以来中国书画主流风格的渊源流变,由此确立了以风格流派断代,辨伪的方法。正如他本人所说“最切实的办法是,认识从一家开始,而后从一家的流派渊源等关系方面渐次地扩展”。虽然他也不忽视对相关文献的印证,但却更看重书画艺术的本体,如作品的意境,格调、笔法、墨法、造型和画面布局等特征,即重视书画本身的体貌精神。此种鉴定方法对鉴定者本身的书画水平具有很高的要求,谢稚柳因其本人具有较高的书画创作能力和聪颖的鉴定才智,使其成为这一鉴定方法中的巨擘。谢先生的鉴定理念,他的《水墨画》和《鉴余杂稿》二书有详细记述。
谢稚柳的鉴定艺术确是在创作中一步一步深化的。他的过人之处是着眼直达书画本身,绝对不会敲边鼓。早在1966年,他于香港《大公报》上连载《论书画鉴别》一文,这是一篇有系统的鉴定学论文,从传统的鉴别方法,讲到鉴别方法的论证,讲到辨伪,特别是在讲到对书画本身的认识一章中,谢稚柳画作精论迭出,显示出艺术家对鉴定的敏锐观察力。他从笔墨、个性、流派诸方面来认识作品的体貌和风格。笔墨是形成书画的基本条件,也是形成书画风格的重要内容,更是鉴定书画的主要依据。他认为“首先在于笔,特征是笔的性格,笔所形成的形式,形式所产生的风格,三者是分不开的,三者的综合,是个性,也是时代性。”石涛说“笔墨当随时代”,反过来,从笔墨上也能看出时代风格。如谢稚柳在鉴定《游目帖》时,认为不是王羲之真迹,连唐摹本也不是,而是元人手笔,理由是《游目帖》的笔势与形体已具有赵孟頫的风格。他还能从某一画家的构图定式中点破天机,如对《茂林远岫图》的翻案就是靠此,认为绝非李成之笔,而是出自燕文贵,他举出传世的燕文贵的四幅画,《溪山楼观图轴》、《江山楼观图卷》、《溪风图卷》、《烟岚水殿图卷》,指出它与《茂林远岫图》的一致性。“试从山的形及其皴法,树木的形及其描法,水边的石及其铺陈,流泉的形及其墨的运成以及屋宇及其安排,无一不显示出一手的迹象”。特别是在上列四图中,都毫无例外地在水畔安排着华美的台榭楼阁,而《茂林远岫图》也作了同样的铺陈,这在宋代画派中是独特的表现形式,其实这就是“燕家景”的一大特征。谢稚柳创造性地提出“性格说”,认为鉴定的标准,是书画本身的各种性格,是它的本质,一个画家可以产生水准高的作品,也会产生低劣的作品,问题不在于标准高低、宽严,而在于书画本身的各种性格的认识,性格自始自终贯穿在优与劣的作品之中,基于此,谢氏对于书画作品出现特例时,即某一画家临时变换习惯性画风,或者是早年所作的不成熟样式等等,皆有可能不被迷惑,从而具有深邃的鉴别力。书画实践和他的望气性格使他的鉴定具有一种神奇性,王蘧常在《谢稚柳系年录》的序言中说:“君之鉴别古迹真赝,往往望气而知神遇于牝牡骊黄之外。鉴既定,如南山之不可移,人或不信,但久而后君言卒验,予曰君古迹之九方皋也。”对他的望气给予极高评价,所以从这点上看,谢稚柳是目鉴的天才。
谢稚柳书作的一个起点,对他产生了极大影响,并且影响着他一生的创作和鉴定。他所结交的人物都是书画界和鉴定界名流,除张大千外,还有吴湖帆、张伯驹、章士钊、于右任、沈尹默、徐悲鸿、容庚、商承祚、于非暗等,在他的艺术历程中起着无形的作用。36岁时结识张伯驹是他鉴定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张氏收藏颇丰,又精于鉴定。41岁时,上海文管会成立,聘请他为编纂,此终身一大转折,须知中国历来没有鉴定专门学校,像谢稚柳这样半途出家,便是难得的鉴定天才了。他从此便以鉴定知名。53岁时,国家文物局组织书画鉴定小组成员,对全国各地所藏古代书画作全面系统的鉴定,跨越四省,往返半年,所见书画万余轴,在他一生的鉴定生涯中是件大事,就是在历代书画鉴定家中也是罕见的。
当20世纪80年代中国书画历经“文革”劫难后再次空前聚集时,中国古代书画巡回鉴定组终于宣告成立。国家文物局调集了当时中国最具权威的书画鉴定家谢稚柳、启功、徐邦达、刘九庵、杨仁恺、傅熹年、谢辰生等组成专家组。到1990年北京总结会,及对少数省会的一些补遗工作,使这次前后八年,行程数万里,过目书画十余万件的鉴定界盛事有了“八年抗战”之誉。
对个人风格研究固然是鉴定核心,在谢稚柳先生看来流派研究同样不可或缺。时代风尚来之于个人特性,而个人风貌又为时代风格所规范,二者之间既是师承传脉,互相影响,又互为制约,其辩证关系不啻是书画鉴定的主脉和灵魂。对此,有几十年实践经验的老先生们再也熟悉不过了且运用自如。此时谢先生反复强调鉴定必须要扩展地去研究。扩展研究的分寸最难把握,其界定范围之广,内涵因素之复杂,不是一般初涉者能够理解、掌控的,特别是排除所谓开门的真假,对那些画家随心所欲的应酬之作,或初期、或转型期、或由于种种主客观因素不同之作与那些高水准的赝品之间就有一个让人捉摸不定的模糊空间,对这些画要慎之又慎,要用扩展的眼光去把握它们本来就已脆弱的脉搏。鉴定中关键既要看笔道,也要看气息,从中寻找变与不变之间的轨迹,回归到客观时空去设想可能产生的结果,这样才能减少由于主观意念的判断失误而导致书画鉴定的差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