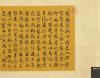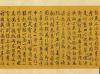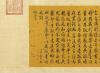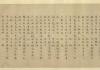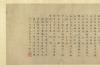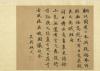润祥鉴赏:中国画派与名家欣赏 1121 宋 郭忠恕
他继承了展子虔、李思训、卫贤等表现建筑传统而有所创造,不仅比例、结构精确,而且生动自然,他的作品,被公认是界画发展新水准的标志,是宋代界画方面的代表性画家。所绘重楼复阁,颇具营造规范。存世《雪霁江行图》,传为其所作。兼通文字学,善写篆、隶书。所著有《佩觽》三卷,阐述文字变迁源流,并考证文字传写错误,对辨别常用的形音义相近字有参考价值。又汇编古文字为《汗简》,为研究古文字学者所重视。
【名称】宋 郭忠恕 雪霁江行图
【年代】宋
【简介】绢本,水墨画,轴,74.1×69.2cm。
长于界画的河南籍画家郭忠恕,以纯以墨线描绘两艘冒雪前行、满载货物的船只。画中不但表现了对船体正确结构的兴趣,也呈现出船夫们多样的活动情态,可藉此图想见五代宋初北方界画达到的艺术水平。
特征说明:桅杆上紧系的绳索,各有一条超越船体向右下延伸,参考藏于纳尔逊美术馆由后代摹制的〈雪霁江行图〉,可知此作仅存左半部,原图绳索应延伸到前景坡岸上,由纤夫拖曳,拉船前行,右上方另有山景点缀。
《圣朝名画评》提到郭忠恕是以木匠使用的建筑结构计算方式描绘宫室屋宇题材。此图虽以船体为主,但对桅杆、卡榫、绳索捆绑等部位皆有清楚的交代,可以看出对精确表现物件构成的特别取向。
《宣和画谱》中批评徽宗朝的画家作界画多用直尺、笔迹繁杂、缺乏像郭忠恕等早期画家呈现出的壮丽闲雅之感。此图中舱壁上的开光雕饰,虽朝船尾渐次缩小,表现出远近感,但并非全以规矩绳墨画出,而是徒手绘制,符合画史中对郭忠恕的描述。
【名称】宋 郭忠恕 明皇避暑宫图
【年代】宋
【简介】绢本,墨笔,纵:161.5厘米,横:105.6厘米。日本大阪国立美术馆藏。
此图无款识,传为郭忠恕所绘,画幅题签:“郭忠恕越王宫殿图,穰梨馆藏。”画中宫室建筑宏伟壮丽,结构复杂,细密精工,造型准确,避暑宫背山面水,景色宜人。图中山石呈卷云状,其宫殿楼阁描绘精密工致,法度严谨,已是北宋中期郭熙画派的风致,故此图绘制时间应晚于郭忠恕,当在宋元之际。画幅右下钤“过云楼收藏印”著录于《穰梨馆过眼录》。
五代 郭忠恕 临王维辋川图
(传)郭忠恕 临王维辋川图 墨拓本
宋 郭忠恕 臨王維輞川图卷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史载王维曾于蓝田筑辋川别业,并作〈辋川集〉诗廿首,又于清源寺壁上绘辋川。其图或早已无存,其事却为后人怀想不已,故传世有多本〈辋川图〉,其中多有自称为北宋界画名家郭忠恕(卒于西元九七七年)临王维辋川图者,本幅即为其一。
此幅以长卷形式,串连〈辋川集〉裡提到的各景,再加上「辋口庄」,共廿一景。多採圏围式空间的构图,与人朴拙古雅之感。然自其用笔而观,或为明清人所为。
潮河边人考:本幅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品类似,而后者两幅中《辋川别业图》为明人画、《辋川别墅图》为明清画。
元/明 佚名 仿郭忠恕携琴仙馆图 弗利尔美术馆藏
五代 郭忠恕 避暑宫图
五代 郭忠恕 雪霁晓行图(清人画)
148.5 x 103.2 cm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楼台仕女图》,绢本,设色,册页,长29厘米、宽31厘米。传为五代末期至宋代初期的画家郭忠恕所绘。
忠恕,字恕先,又字国宝。洛阳(今属河南)人。7岁能诵书属文,举童子及第。后周广顺中(公元952年左右)召为宗正丞兼国子监书学博士。工画山水尤擅界画,楼观舟楫皆极精妙。所画楼阁建筑,颇合规矩,比例准确精细。《圣朝名画评》中说他的界画,为“一时之绝”,被列为“神品”。《宣和画谱》认为“三百年之唐历五代以还,仅得卫贤以画宫室得名。本朝郭忠恕既出,视卫贤辈其余不足数……如忠恕之高者,岂复有斯人之徒欤?”他的“界画”对后世影响很大。传世作品有《雪霁江行图》卷,《明皇避暑宫图》轴等。又编著《佩觽》和《汗简》。《楼台仕女图》就是他“界画”风格的典型作品。
界画,主要是描绘景物中的建筑,如宫殿、寺塔、亭台、楼阁等等。这些建筑物,大都掩映在山峦或园林当中,巍然矗立、鳞次栉比,给人以宏伟、端庄、典雅的美感。画这种画,特别是其中的建筑物,与通常的山水画不同,它要求结构必须完整准确,不能是“写其大意”,《宣和画谱》云:“宫室有量,台门有制……一点一笔,必求诸规矩,比他画为难工。”这说明成为界画画家不但能画,也必须具备建筑方面的知识。并且对那些房屋的脊、檐、廊、厦、梁柱、斗拱、门、窗、台阶等物,都要借助界尺来画,使线条均匀、挺直,与原物相似,要表现出质感。人们管这种画,叫做“界画”,成为一个独立的画种。
界画产生,年代很久,早在东晋时期,画家顾恺之,在论绘画经验时说:“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榭一足器耳,难成而易好。”唐代的界画,就已非常成熟,现存敦煌壁画中的佛殿、楼阁即是例证。发展到宋初,郭忠恕成就突出,影响也最大。其他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等,还为我们研究古代建筑、社会风俗以及生活各方面,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此后,元代有王振鹏、李容槿,明代的仇英,清代有袁江、袁耀等都是界画大家。
《楼台仕女图》中所绘建筑物,究属何地、何楼,已无从查考。其实,现存的著名楼阁,多年遭受风雨、灾祸,几经修缮与翻建,面目早已全非,何况如此没有款识的图画了。我们根据建筑样式,较之诸类名楼如:“ 滕王阁”、“ 黄鹤楼” 、“岳阳楼”以及“阿房宫”、“鹳雀楼”等来看,皆有同异之处。此图原为圆光(团扇),近景繪几株高大松树,在樹的頂端,画出阙楼建筑以及楼阁前面高台上的仕女——宫人们的活动情景。画中人物与雄伟的楼台相比,极其微小,但刻画的非常生动、传神。由于他们没有接迎任务,更没有进行排演,因此场景比较清静,有的手执纨扇,意在纳凉,三三两两,聚散信步,有说有笑,悠闲自在。
一向被评家议论不休的中国画“散点透视法”,在《楼台仕女图》中可以得到一个例证,即:画家站在制高点上,向前下方俯瞰,以特写的形式,将景物——松树、楼阁、河湖以及对面远处的沙渚如实的映射在画面之上。正像东晋时期的宗炳在他的《画山水序》中所说:以真山水的形状,画山水之形状;以山水本来之颜色,著山水画的颜色。把昆仑之大,用我们的眼睛将它缩到“一寸”之间,这是因为眼睛可以包容数里之中所有景物。“诚由去之稍阔,则其所见弥小”,若拿着一块透明的白绢,对着景物,“框”(远映)一下的话,“则昆阆之形,可围于方寸之内。竖划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
另外,我们再从阁台上人物的比例来看,也正符合王维所讲的“丈山尺树,寸马分人。 远人无目,远树无枝。远山无石,隐隐如眉(青黛的颜色)。远水无波,高与云齐”的道理。董其昌以为“画”不似真形,像苏东坡所说的:“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这是“元人画”的特点。如晁以道的诗:“画写物外形,实物形不改”要求“形似”,则是“宋人画”的标准。董其昌的论点虽不十分严谨,但依此来读郭忠恕的这幅《楼台仕女图》我们觉得还是很合适的。
郭忠恕,兼精文字学、文学,善写篆、隶书,尤其“界画”为世人推重,“界画”是随着山水画发展而派生的一科,主要是画与山水画中有关的亭台楼阁、舟船车舆。《圣朝名画评》中评他的界画,为“一时之绝”,列为“神品”,传世作品有《雪霁江行图》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