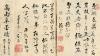润祥鉴赏:中国画派与名家欣赏 1134 清 高凤翰 4
不料,正当他潜心艺术之际,右手突患麻痹之症,不能再作字画。接连的打击,使得他有些措手不及。试想,他一定苦恼过,失望过。最终,他还是用左手拿起了毫管,重新起步,再做探索。尽管是同一个大脑支配,左手却不像右手那么听使唤。写出来的字,与想象中的简直是大相径庭,甚至大有桀骜不驯之势。他也许有气极败坏之时,将笔掷于案上,而跺足长叹。他也许是在偶然一瞥中发现,这种不驯服的笔触,不正是他以往苦苦追求的天趣与老辣吗?平时,右手太听话,太认真了,所以很难体现出这种效果。左手却在生涩中,露出了这种渴求的表现方法的端倪,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坏事中的好事呀!
无意中厾破了悟性的窗纸,高凤翰超脱了,兴奋了,以他顽强的意志,明澈的肝胆和刚刚开发的右脑支配下的左手,进入了创作的黄金时期。
我们来看看这《书怀·石头城外放船行》草书轴,从流利的行笔和自然的气势中可以肯定是他右手未病前所书,从始至终有一种飘飘欲仙的韵味,但是不狂不怪,可谓放而不纵。如果高凤翰从未发病,这件作品很叮能就是一件佳作,他的书风就不会再发生质的变化。
就像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词分前后期一样,高凤翰的书风也存在一个分水岭。李清照是以南渡为分界线的;高凤翰则以左右手的转换,完成这种变革的。让我们来看一看,他后期的草书《窗夜·纸帐生虚白》。同是一件草书轴,风格却有了质的飞跃。可能高凤翰本人也不敢正视这个现实,所以落款时加了"左手"二字。
左手的用笔随意性大大增强厂,很可能是它不太听话的缘故。首先用笔的轻重变化相当明显,有几个字格外突出,十分醒目。高凤翰并非驾驭不住自己的人手,而是有意借助它的"活跃",从而变劣势为优势,加强提按,产生意想不到的变化。这几个字的突出,并没有打破整体的协调,由于这种加力是经过酝酿的,安排得比较巧妙,所以就像是一段乐曲中的几个强音,使人振奋,使人赏心,运用得真是恰到好处。特别是那个"兀"字,内容与形式达到了近乎完美的一致,仿佛足潮水回落时,高兀的礁石一样,急匆匆地扑入人们的眼帘,简直让你无法回避。
高凤翰不仅是书法家,还是清代前期著名的画家、诗人。他曾写过这样一首诗:
老樵卧白云,修柯不以斧。
笑拾泰山松,拄之下梁父。
这首诗正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他就是这样笑对人生的。他有意无意地将诗、书、画的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提高,他是刻苦勤奋型的大家,和郑燮、金农等为伍,在繁华富庶的扬州,立住了脚跟。《墨林今话》里曾写出了他彼时的知名度,由于向他求画的人太多,;有人就转向郑燮代求。郑燮便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西园左笔寿门(金农)书,
海内朋友索问余。
短札长笺都去尽,
老夫屑作亦无馀。
既然如此,让我们再来看一看高凤翰的"凤翰左手行书信札册",这种感受也许会更加深刻。首先书札是最能体现书家风貌的所在,他可以无拘无束,信手挥就。他不必考虑篇幅,有活则长,无话则短,一派纯任自然的心态。再者行书又是书札之中最佳选择的书体,楷书书写速度较慢,不适于书札。草书,又太快,书者可以尽抒胸臆,甚至随时尽情发挥,可读者则瞪日搔首,因一字之不辨,而不解或误解全札中的所指。因此,行书为书札之首选字体,无疑是在情理之中了。正因如此,高凤翰的行书书札,就有着不加雕琢,质朴自然的风神。难怪有人说他的书札之中,有一缕超脱之气,冉冉而上。
这是全册中的二件,寥寥数语,写得潇潇洒洒,由于格式和内容的缘故,出现了一些空白。正是这些空白的出现,给书札平添了虎虎的灵动之气。一些小字的加入,更是显得变化无常,风神奕奕。
两件"阿仲左手行书信札"也极富个性,有的竖行不直,似有挪让之态,但仍是一气贯之,而毫无懈怠之处。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互为扶持,大有腾空欲飞之势。难怪《清朝书画录》中说他的草书"圆劲飞动"。其势在行书中已经充分体现了出来,更何况草书呢?点画之间的呼应,大小字间的错落,均有过人之处,叫人扼腕慨叹。
高凤翰颇具才华,即使是在"海内文土,半在维扬"的文人聚集之处,他也没有被埋没。他敢于立异标新,不拘成法,终于使自己的艺术得到社会的认可,这是殊为不易也。他凭着自己的实力,跻身"扬州八怪"之列,是完完全全在情理之中的。
高凤翰除了行草之外,还善写隶书。对于隶书,他有着同样的创作指导思想。他的隶书宗汉,并兼学同代人郑簠的,但相比之下,他用笔比较迟涩。笔画粗细不-,锋或藏或露,往往以撇画的延伸或捺画、横波的急挑,而打破原有的平衡。使得他的隶书有汉之韵味,又汇入新意,毫无矫揉造作之态。
高凤翰还有印癖与砚癖之称,收藏了许多印石与砚,他很喜欢刻砚铭,技巧相当熟练,治印也极富特色,《续印人传》中说他,"究心缪篆印章,全法秦汉,苍古朴茂"。他曾刻"丁巳残人""残道人""左臂"等印,他不回避自己的残疾,反而屡次将"残"入印,说明他具有正视现实,不畏困难的勇气,这几方印章是他右手病残以后所治,和他的"左书"一样,敢于用刀,全以气胜,仿佛在不经意间,就已经刀落印成。
高凤翰是画家、书法家、篆刻家,也是诗人。他的满腹才华从多方面体现出来,真是艺绝千古,昭厉后人。直至今天,我们仍能从他的各类作品中找到笔情墨趣,从中得到熏陶,开阔视野,精神上得到了一次次极大的艺术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