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可之学书札记4┃墨海灯塔——致敬孙过庭《书谱》之泽
2025-10-09 00:41:57
张可之,字文斋。兜底儿网签约书法艺术家,国家开放大学书画艺术教育研究院研究员。1958年出生,羲之故里人。自幼笃爱书艺,60年如一日,痴迷如醉。曾多次入选国内外大展并获奖。2023年央视网络版连续100期推出他用楷、隶、篆、行四种书体创作的作品。
六十载临池不辍,案头那卷早已泛黄的手抄《书谱》,始终如良师伴侧。每当指尖抚过纸页上略显稚嫩的字迹,初中时在老家私塾先生书桌前抄录典籍的画面便清晰浮现,这份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墨缘,让孙过庭笔下“穷变态于毫端,合情调于纸上”的箴言,成了我书法之路上最珍贵的指引。这部诞生于初唐的书法论著,其“来龙去脉”间藏着中国书法理论的巅峰成就,而它于我而言,早已超越典籍本身,成为连接理论与实践、陪伴岁月流转的精神印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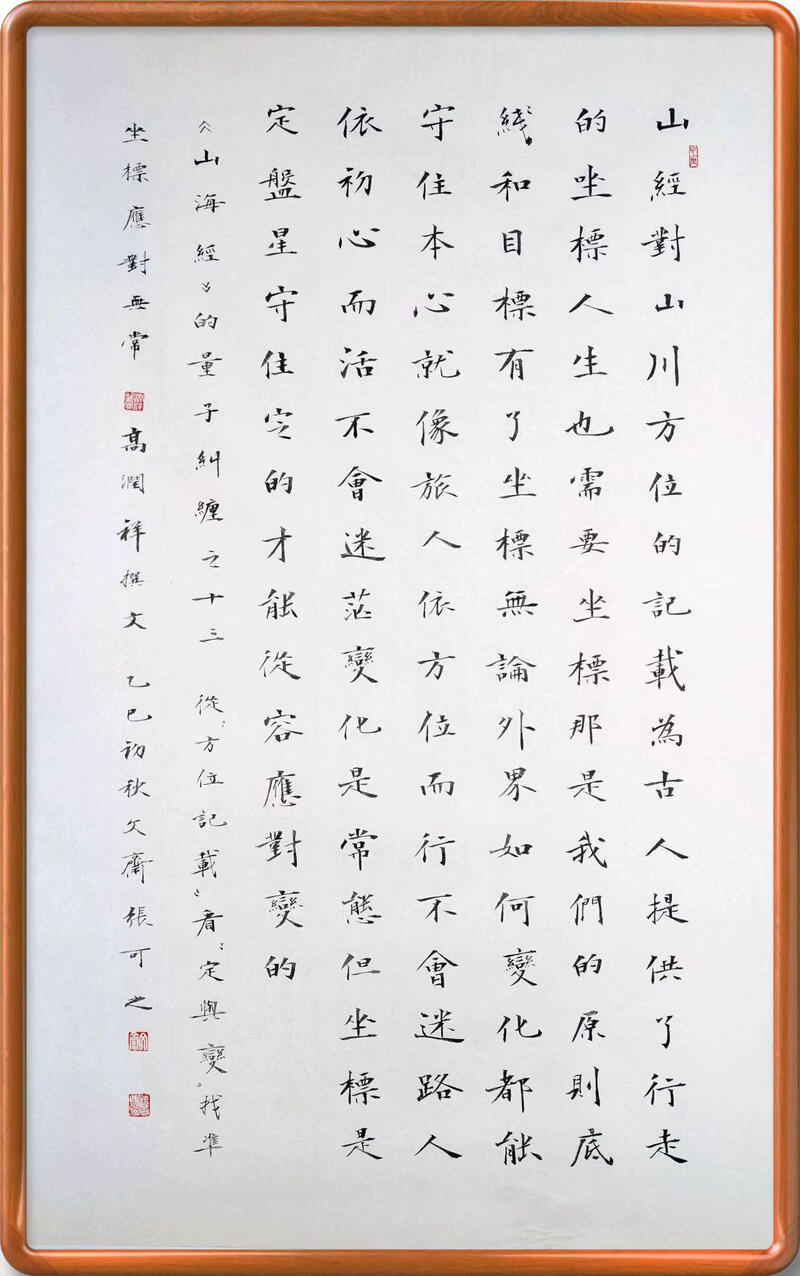
图片一
规格:97×60 cm(5.23平尺)
释文:《山经》对山川方位的记载,为古人提供了行走的坐标。人生也需要“坐标”——那是我们的原则、底线和目标。有了坐标,无论外界如何变化,都能守住本心。就像旅人依方位而行,不会迷路;人依初心而活,不会迷茫。变化是常态,但“坐标”是定盘星:守住定的,才能从容应对变的。《山海经》的量子纠缠之十三 从“方位记载”看“定与变”:找准坐标,应对无常。 高润祥撰文 乙巳初秋文斋张可之
释印: 文斋 张可之印 润祥鉴赏 文斋闲人之印 心画
追溯《书谱》与我的渊源,要从六十多年前说起。那时我尚是孩童,便常听家中长辈提及“孙过庭”与“《书谱》”的名号,只知那是一部能让人“懂书法、写好字”的奇书,心中满是向往却无缘得见。直到上初中那年,偶然得知远房亲戚家一位读过私塾的老先生,藏有一本亲手抄录的《书谱》,我便揣着忐忑与期待,多次登门恳请借阅。老先生见我真心爱书,最终应允我在他的书桌前抄录,还特意叮嘱:“一共三千多字,不要急,抄的时候要走心,字里行间都是道理”。
那段日子,我每天放学后便直奔老先生家,伏在旧木桌上,一笔一画地将《书谱》的文字与老先生批注的要点抄录下来。宣纸铺展,墨香萦绕,孙过庭论述书法的字句从笔尖流淌而出,“初学分布,但求平正”“达其性情,形其哀乐”的句子,虽当时未能完全领悟,却像种子般埋进了心里。抄完后,我将这本手抄本视若珍宝,用蓝布包好藏在书包里,无论是课间休息还是夜晚灯下,总忍不住拿出来翻阅,即便有些理论晦涩难懂,也舍不得放下。这份“抄录”的经历,让《书谱》从“传说中的典籍”变成了我触手可及的伙伴,也为我后来的书法学习埋下了最重要的伏笔。
再看《书谱》本身的“来龙去脉”,更觉这部典籍的珍贵。作者孙过庭出身寒微却嗜书如命,精研“二王”书法,兼通各体,尤擅草书。他因不满当时书法理论零散细碎、或空或浅的现状,立志撰写一部“理技兼备”的著作,历经十余年打磨,终在垂拱三年(687年)定稿《书谱》。这部作品以草书书写全文,三千七百余字纵贯纸本,笔势遒劲婉转,墨色枯润相间,既是理论专著,亦是草书艺术的巅峰之作——后世评其“书论双绝”,绝非虚言。
流传过程中,《书谱》原稿曾遭火劫,后半卷不幸焚毁,现存前半卷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虽非完璧却光芒不减。宋代以来,它的刻本层出不穷,从《宣和书谱》著录到《三希堂法帖》收录,始终是书法家临摹学习的范本。而我手中这本私塾先生的手抄本,虽非名家刻本,却因承载着“抄录”的温度与岁月的痕迹,成了我最珍视的版本。六十年来,我始终如一地经常把读这本手抄《书谱》,纸页虽已磨损,墨痕却愈发清晰,每一次翻阅都有新的领悟,仿佛与孙过庭跨越千年对话,也与当年那个抄书的少年隔空相望。
在六十年的书法学习中,我最深的感悟便是:从《书谱》中获取书法理论指导,与临帖、仿写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很多人认为“学书法只要多临帖就行,理论没用”,但我用亲身经历证明,没有理论指引的临帖,就像在黑暗中走路,即便走得再久,也难辨方向;而脱离临帖实践的理论,不过是纸上谈兵,无法真正转化为书写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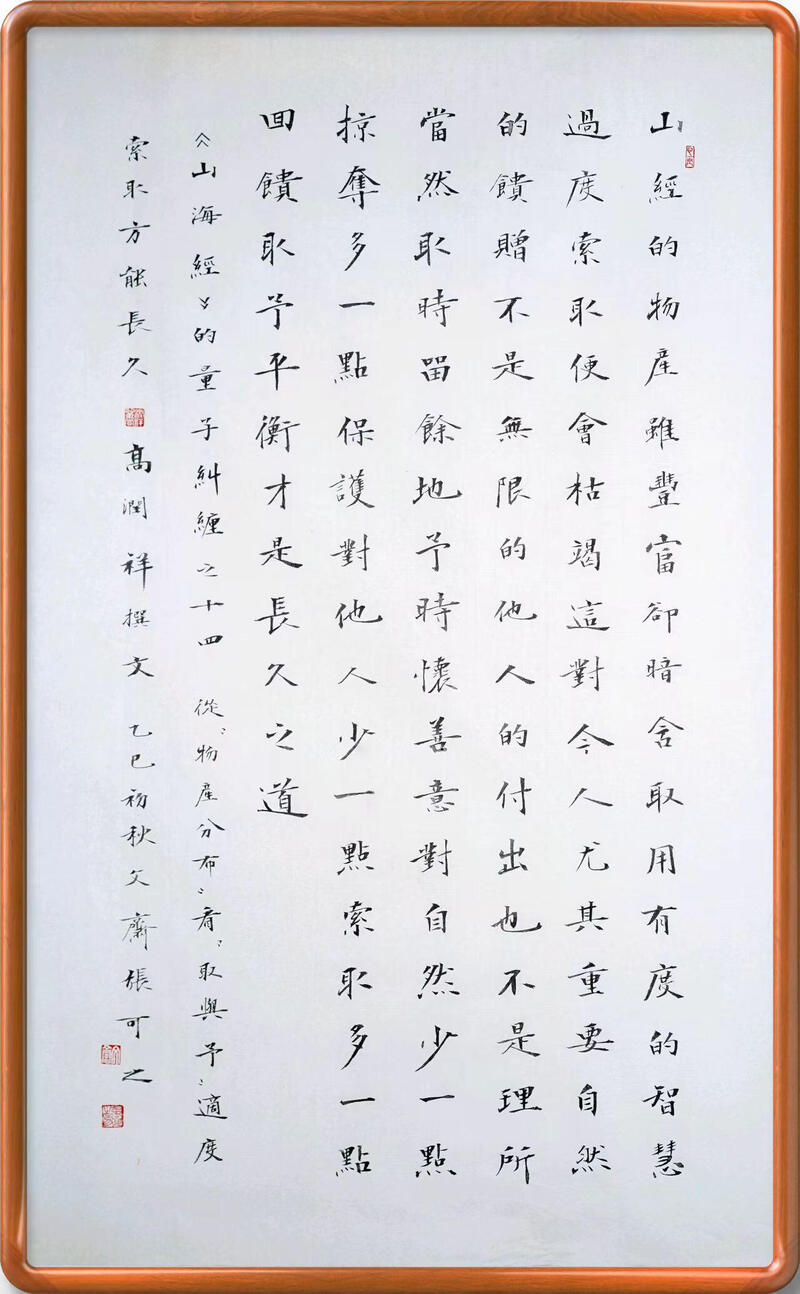
图片二
规格:97×60 cm(5.23平尺)
释文:《山经》的物产虽丰富,却暗含“取用有度”的智慧——过度索取,便会枯竭。这对今人尤其重要:自然的馈赠不是无限的,他人的付出也不是理所当然。取时留余地,予时怀善意:对自然,少一点掠夺,多一点保护;对他人,少一点索取,多一点回馈。取予平衡,才是长久之道。
《山海经》的量子纠缠之十四 从“物产分布”看“取与予”:适度索取,方能长久。高润祥撰文 乙巳初秋文斋张可之
释印: 文斋 张可之印 润祥鉴赏 文斋闲人之印 心画
《书谱》的理论指导,首先为我的临帖与仿写划定了“方向”。初学书法时,我曾盲目临写柳公权、颜真卿的楷书,却总觉得写出来的字“有形无神”,结构松散、笔画僵硬。直到反复研读《书谱》中“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的三阶段论,才明白自己的问题所在——跳过了“平正”的基础,直接追求“险绝”的风格,根基不稳自然难成气候。于是我调整方法,先从楷书的横平竖直练起,严格按照《书谱》中“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的要求,在临帖时注重笔画位置与结字结构,待基础稳固后再探索章法变化。渐渐地,我临写的字有了“骨架”,仿写时也能把握字体的神韵,这正是理论指导带来的突破。
其次,《书谱》的理论让我的临帖与仿写更懂“取舍”。学习行书时,我曾同时临写王羲之《兰亭序》与苏轼《寒食帖》,前者飘逸灵动,后者沉郁顿挫,我试图将两种风格融合,结果写出来的字不伦不类。这时我再次翻开《书谱》,看到孙过庭评价王羲之“思虑通审,志气和平”、历代书家“各有其长,贵在专精”的论述,瞬间豁然开朗——临帖与仿写不是“照搬所有”,而是要在理论指导下理解不同书家的风格内核,再结合自身特点选择方向。于是我先以《兰亭序》为基,吃透“二王”行书的法度与韵味,再借鉴《寒食帖》的情感表达,而非生硬模仿笔画形态。如此一来,我的仿写作品既有传统根基,又有个人思考,这正是理论赋予的“辨明优劣、合理取舍”的能力。
更重要的是,《书谱》让我明白,临帖、仿写与理论学习的最终目标,都是“达其性情,形其哀乐”。过去我临帖时,只关注“笔画像不像、结构对不对”,却忽略了书法的情感表达,写出来的字看似工整,却毫无生气。直到读到《书谱》中“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的论述,才懂得书法是“心手相应”的艺术。此后我在临帖前,会先研读文本内容与书家创作背景,临写《祭侄文稿》时,便带着悲愤沉郁的心境;仿写田园诗时,便用舒缓流畅的笔势。渐渐地,我的字有了“温度”,这正是理论与实践结合后,才能达到的“技道合一”的境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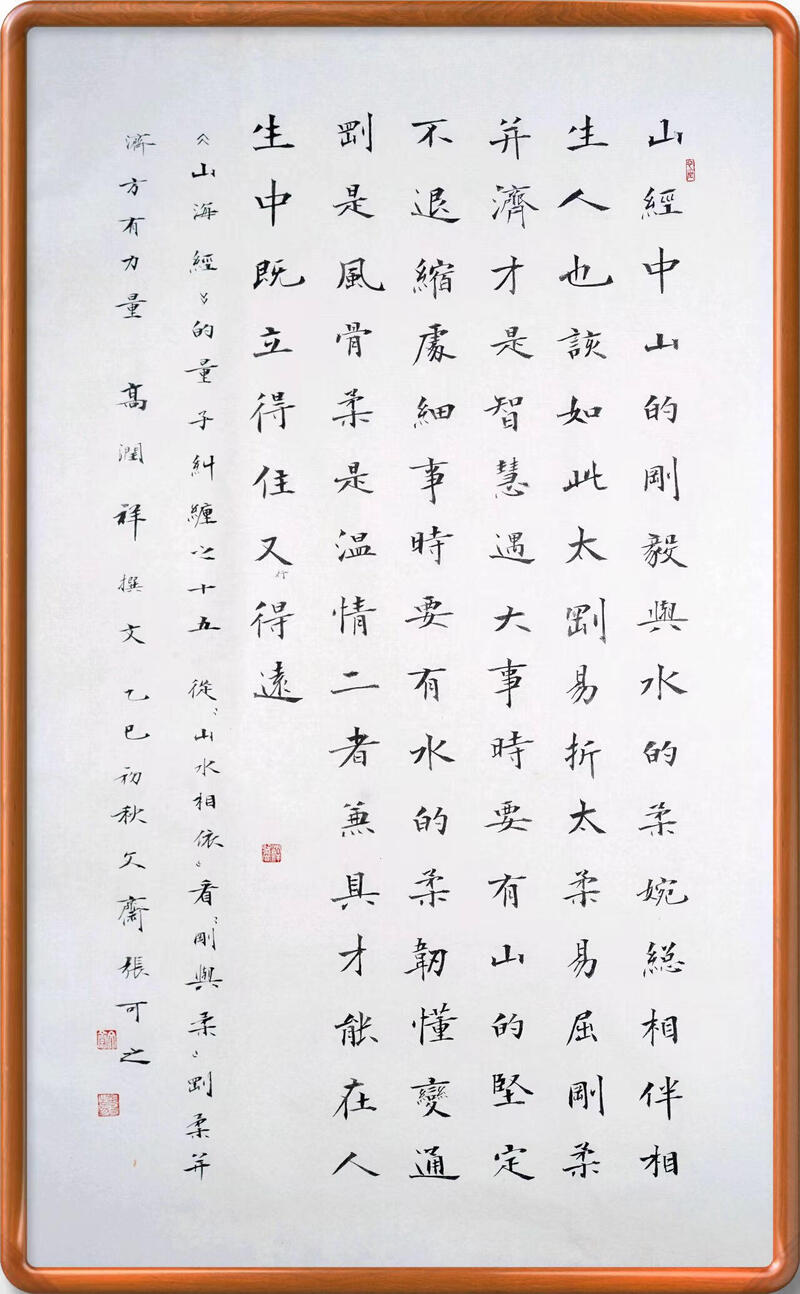
图片三
规格:97×60 cm(5.23平尺)
释文:《山经》中,山的刚毅与水的柔婉总相伴相生。人也该如此:太刚易折,太柔易屈,刚柔并济才是智慧。遇大事时,要有山的坚定,不退缩;处细事时,要有水的柔韧,懂变通。刚是风骨,柔是温情,二者兼具,才能在人生中既立得住,又行得远。 《山海经》的量子纠缠之十五 从“山水相依”看“刚与柔”:刚柔并济,方有力量。高润祥撰文 乙巳初秋文斋张可之
释印: 文斋 张可之印 润祥鉴赏 文斋闲人之印 心画
六十载岁月流转,当年抄录的《书谱》仍在身边,孙过庭的智慧也早已融入我的笔墨与人生。它不仅教会我如何写字,更教会我如何以“平正”之心待人、以“专精”之志做事。孙过庭在《书谱》中写道:“通会之际,人书俱老。”如今我虽已至暮年,却仍在朝着这个境界努力——每当提笔,看到案头的手抄本,便想起初中时抄书的初心,想起理论与实践交织的每一步。
这部诞生于初唐的墨宝,于我而言,早已不是一部简单的典籍。它是少年时的向往,是抄录时的虔诚,是六十年临池路上的指引,更是让理论与实践同频共振的桥梁。回望来时路,最幸运的莫过于与《书谱》相遇,它如清泉滋养笔墨,如明灯照亮前路,这份跨越千年的墨缘,终将伴随我继续走下去,直至“人书俱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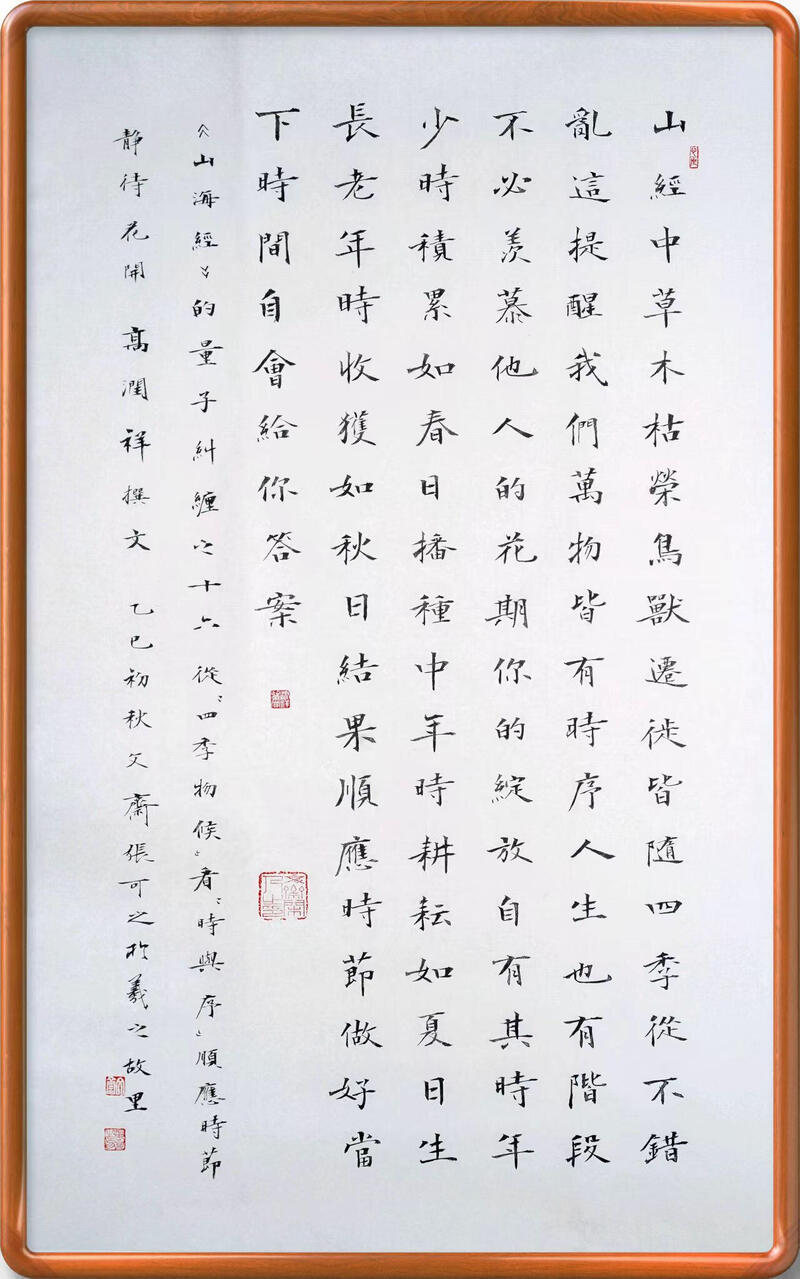
图片四
规格:97×60 cm(5.23平尺)
释文:《山经》中,草木枯荣、鸟兽迁徙皆随四季,从不错乱。这提醒我们:万物皆有时序,人生也有阶段。不必羡慕他人的“花期”,你的绽放自有其时。年少时积累,如春日播种;中年时耕耘,如夏日生长;老年时收获,如秋日结果。顺应时节,做好当下,时间自会给你答案。《山海经》的量子纠缠之十六 从“四季物候”看“时与序”:顺应时节,静待花开。高润祥撰文 乙巳初秋文斋张可之
释印: 文斋 张可之印 润祥鉴赏 文斋闲人之印 心画
相关热词搜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