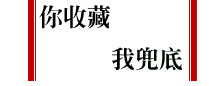傅以新
1961年,我考入了中央美院国画系人物画科。到校报到的第一天,经过同学指点,我终于见到了自己心仪已久的任先生(当时叶先生任国画系主任)。他中等身材,身姿挺拔,衣着合体,还很洋气,小胡子微翘,走路带有弹性。他总在后裤兜里插着一个不太大的速写本,可以随时掏出来画速写。给学生上大课或开会时,他会逐个与学生对目光。他的双目炯炯有神,好像能一下子看到你的心里。他讲话很干脆。看到有的学生没有主见地“跟风”,他就会说:“你不适合画这个,选别的路吧。”
第一次和同学们去叶先生家拜访,我就提出想看看先生的速写,他立即搬出两大摞。那些速写都经过精心整理,装在等大的卡纸上,并按类分置,如“广西”、“内蒙”、“京剧”等。叶先生的夫人王人美默默地在我们每个人面前放了一杯热茶,我只是贪婪地翻看着那些速写,恨不能把它们都记在脑子里。等到告辞出来,我才想起,两个多钟头的时间里,自己都忘了喝那杯热茶。
在我眼中,叶先生既是一位严厉的老师,又是一位慈祥的长者。他经常十分慷慨地把作品借给学生去临摹,让学生从简洁的笔墨处理中体会夸张和精确的对立统一,我更有幸得到过他赠予的戏票——首都剧场,一排一号!这是人艺为他画舞台速写专门留的位子。那天上演的是话剧《红色宣传员》,狄辛主演。临开场时,周恩来总理陪同朝鲜领导人来了,座位正在我的后面,四排一号。大幕拉开,我专注于舞台,动笔画起来。第一次在现场画舞台速写,顾此失彼,画了不少,却不成形,回来也未敢让先生看。但叶先生后来再三告诉我说:“舞台速写往往只能记几个大动态线,回来的整理最见功夫,关键是要保持当时舞台的感受和速写的生动性。”正是因为他的鼓励,多年来我一直坚持画速写。
“文革”伊始,叶先生等人就被打成了“牛鬼蛇神”,关入了“牛棚”。叶先生的遭遇尤其悲惨,在“黑画展”上竟遭到“红卫兵”毒打,鲜血染红衣。1968年,他又因“历史问题”被正式逮捕。
所谓的“历史问题”,是指叶先生在中美合作所的一段工作经历。二战后期,美国政府与国民党政府成立了中美合作所,进行对日的情报战和心理战。1944年底,叶先生被聘入中美合作所心理作战处,绘制抗日漫画,印刷后空投日占区,以瓦解日军的战斗力。因叶先生是名人,所以薪俸很高,不过他在那里只干了五个月。抗战胜利后,中美合作所成了国民党关押、残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罪恶机构,但叶先生当时早已离开那里了。这段历史在解放后已作过结论,“文革”中却依然给他带来了七年的牢狱之灾。
1971年,我从下放锻炼的部队利用探亲假去广州看望二哥,顺便拜访了广州美院的关山月院长,那时他刚从“牛棚”出来不久。他非常关切地向我询问中央美院的每个老朋友的情况。正说话间,著名漫画家廖冰兄先生来了。关院长向他介绍我说:“这是叶浅予的学生。”廖先生听后高声说道:“啊哈!我可被你的老师害苦了!”看我瞠目,廖先生便提起了一段二十多年前的旧事。那是1945年初,叶先生向中美合作所提出辞职,对方要求他必须找人来接手他的工作。一天,在重庆街头,廖先生和叶先生夫妇偶遇。闲聊中,叶先生得知他还没有找到工作,就问他有个薪俸高的画画的工作愿不愿去。于是,廖先生就接替了叶先生的工作,继续为抗战创作漫画。廖先生只在那里干了一个多月,“文革”中也因此被关了几年。说起自己的遭遇,廖先生忽而激动,忽而唏嘘。我对他说:“我的老师更惨,至今还在狱中,不知他还能不能出来!”在场的人听后无不扼腕而叹。
“文革”结束后,叶先生终于被释放并获平反。虽然他在“文革”中历经磨难,但他并没有过多地抱怨,还毅然把落实政策退还的三万元工资捐出,首开个人在中央美院设立奖学金之举,受到众人的交口称赞。
1981年,74岁高龄的叶先生调任中国画研究院(现为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几年以后,我出差到北京,顺便去研究院看望老同学邓林,向他问起叶先生的近况。他说:“这几天叶先生正好在研究院,这会儿可能在吃饭。”我俩赶到食堂,叶先生果然正在就餐。他苍老了许多,鬓发皆白,面颊消瘦,但目光依旧是那样有神。时隔多年,他几乎已经记不得我的名字了。知道我分配在天津美院后,他向我问起其他同学的情况,我也问他最近在忙什么工作。他说:“我正在写回忆录。过去写了一点儿,作协的人看了,还要我加入他们作协呢。”说着,他爽朗地笑了起来,声音略显沙哑,却充满了感染力。又几年后,我便看到了他的回忆录《细叙沧桑记流年》,生动、直率,正如他的为人……
今年正好是叶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仅以此文略表我深深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