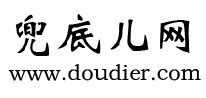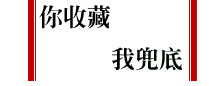在书法史上,杨凝式曾被称做“杨风(即‘疯’)子”,但我们千万不可以为杨凝式真的就是一个疯子。如同我们于现实当中经常碰到的一样,道理很简单:如果真是一位疯子,那他什么事也不干了,更不会如今人朱以撒所说的由他一个人撑起了一个书法时代。应该说,他比谁都清醒,他的疯是故意“装”出来的。正因为如此,他才留下了那些难得的经典式佳作,供后人玩味不尽。
现在的问题是,杨凝式为什么要装疯呢?
原来,杨凝式的时代是一个乱世,出于生存需要,他不得不装疯卖傻,给人(主要是当权者)一个假象——杨凝式已非常人,用不着时刻提防他,也用不着设计谋害他了。
据史载,杨凝式生于唐懿宗咸通十四年(875),卒于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4)。父亲杨涉为唐末宰相,家世可谓显赫无比,这当然是杨凝式值得骄傲的地方,我行我素,不与同僚一般见识,不与同僚混迹官场、碌碌无为。加之遇上特殊的时代,朝廷到处是混乱、是猜忌、是仇恨,杨凝式原有的变态心理又被进一步强化,使得他对处身其中的官场充满了担忧、恐惧,且已无法像正常人一样若无其事地混日子。他虽然一如既往地平稳做官,但总以为这一切有一天会莫名其妙地失去。这样,装疯卖傻便成为他的一个极自然的选择。
本来是一个极不自由者,说话、行动处处都得循规蹈矩,但披上“疯子”外衣后,一切都可以不顾,这是杨凝式的一个极高明的生存策略。仅一念之间,全身心都获取了大自由。特殊时代的特殊之举果真“救”了杨凝式,使他没有成为众矢之的。他没有真正沉沦下去,他在坚定地走一条属于他自己或能保护他自己的人生之路——他活了88岁,比那些表面清醒而实际昏庸的官僚同辈享年更长,这难道不是一个奇迹么?
变态心理学告诉我们,由于种种偶然或非偶然因素的诱发,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变态心理。但有了变态心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得不到有效的发泄。只要得到有效发泄,绝大部分的变态心理都会在不自觉状态下转化为常态心理。发泄渠道何在?变态心理学家认为,除装疯卖傻之外,最好的还是艺术。真是太巧了,杨凝式为实现自己内心的平衡,把自己的变态心理引向常态心理——装疯卖傻只是一方面,而且也很有节制,他更重要的发泄渠道在于进行书法这项被后人称为“艺术活动”的活动。唐末五代在历史上虽是一个非常短暂的存在,但也有将近百年的时间跨度。其间,挥毫染翰者肯定不计其数。可除了杨凝式之外,今天我们又能知道谁呢?由此想来,对杨凝式来说,变态心理说不定还从根本上促成了他的书史之辉煌哩!
寺观题壁——杨凝式的书法表演
怀素之后,以书写表演为乐趣者,则要首推杨凝式了。
据《宣和书谱》所载,杨凝式是一个典型的狂放型书家,平时进行书法创作,很少独自一人关在家里。他不喜欢尺牍之类的案头小件,而特别倾心大幅书写。由于五代之时尚无后来才有的丈二大纸供他使用,因而,他只好选择墙壁这一载体,并且在众目睽睽之下纵横挥洒,将创作过程(表演)与创作结果(作品)一同奉献给观赏者,“居洛下十年,凡琳宫佛祠墙壁间,题记殆遍”。杨凝式以寺观题壁的方式,既满足了自己的书写表演欲望,也留下了在他处难得一见的巨幅书法佳作。这些寺观题壁,书写之后,即得到“僧道等护而宝之”,所以,直到北宋时期还有无数文人书家前往观赏,并留下许多发自内心的赞叹,比如“少师真迹满僧居,只恐钟、王也不如。为报远公须爱惜,此书书后更无书”(冯少吉诗)、“枯杉倒桧霜天老,松烟麝煤阴雨寒。我亦生来有书癖,一回入寺一回看”(李建中诗)、“余曩至洛师,遍观僧壁间,杨少师书无一不造微入妙,当与吴生画为洛中二绝”(黄庭坚语),等等。
杨凝式留存下来墨迹与帖本,除《夏热帖》稍见狂放外,余者皆表现为循规蹈矩,清刚中见淡远,流便中见萧散。我想,这肯定只是杨凝式向我们展示的两大书法世界之一,另一个书法世界则是被时间淹没、无法为我们今人所感知的题壁书法,那可是一个电闪雷鸣、风狂雨骤,足以惊天地、泣鬼神的书法世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