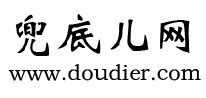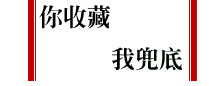清顺治四年,已经42岁的傅山在晋祠小住时,遇到一位好友拿着一篇文章让他观赏,原来这文章竟是20年前,傅山写下的《秋海棠赋》。这位好友请傅山重新书写这篇文章,傅山在书写完之后,又提笔写道:“回视少年时信笔游戏,不无轻佻。”那么,《秋海棠赋》这篇文章究竟写了些什么呢?原来,这篇文章以华丽的词语和拟人的笔法,写了“同称而异志”的两株秋海棠。一株是姐姐,一心与桃李竞芳争艳,一株是妹妹,只求自由而不求别人的赏识。显然,年轻的傅山在描写这两株秋海棠时,以物喻人,以事喻志,笔下已经有了一种自由的灵魂和真实的情感。
傅山一向鄙视只为皇权服务,从而扼杀了文人自由思想的八股文。他曾以愤怒的口气如此痛批八股文:“仔细想来,便此技到绝顶,要他何用?文事武备,暗暗地吃了他没影子亏。要将此事算接孔孟之脉,真恶心杀,真恶心杀!”从他年轻时写下的《秋海棠赋》中,我们可以看到傅山那种追尚自由,不甘凡俗的思想。20年后傅山对自己的这篇旧文章作出“不无轻佻”的评价,不是自谦,也不是客套话,而是他在文学观上的一种根本转变。这种转变就是自由的灵魂依然,而真实的情感则从山林之气和花草鱼虫中跳出,更加贴近了现实,贴近了生活,贴近了社会底层的民众。
傅山生活在明清交替的社会大动荡时代,其诗其文自然也就打上了那个时代深深的烙印。他为明末腐败的政治痛心疾首,对清初朝廷施行的暴政奋起反抗,当康熙亲政,时局渐趋稳定,国家开始走上新的大一统之后,他没有出世为官,而是继续深入民间,将自己的命运和人生交给了养育他的土地和百姓。这种人生必然让傅山与屈原、杜甫、元好问一样,成了具有爱国主义传统精神,反映民间疾苦,在诗词中蕴含着悲昂慷慨之气,字字句句都体味出时代悲剧,一词一赋都闪现着高尚人格的伟大诗人。傅山主张作诗为文要有两条原则,一是“经世济用”,二是“别出机杼”。在这两条原则下,他赞赏司马迁奋笔写下的《史记》、重视孔子及后代儒家们编撰的《尚书》,以及诸葛亮的《武侯书》,认为这些著作才是于世有益的文章。傅山讲究文章和气节的统一,从年轻时代写出《秋海棠赋》开始,一直到77岁生命即将走入尽头时写下的七言古诗《迎春花》,那种自由的灵魂和真实的情感,始终贯穿在他的所有文章中。在《迎春花》中傅山吟道:“坚贞有恒正在此,命寒情热也耐死。”一位77岁的老人歌赞迎春花那种坚强贞洁的性格,那种不求闻达,命运苦寒而情感热烈,永恒不变的生命力,与他22岁时歌赞那株崇尚自由的秋海棠崇尚自由的心态,其灵魂和情感一脉相承。
不避时忌
《因人私记》是傅山传世的一篇重要文章。在这篇记事文中,傅山生动地记叙了为恩师袁继咸蒙冤一案,他率领山西百余名学子赴京伏阙,使袁继咸冤案终获昭雪的过程。傅山真实地揭露了明末政治的腐败和官场的种种黑幕和丑态,刻画出封建官员中贪官污吏的狰狞面貌,也无情地鞭挞了一些随行学子贪图利欲,没有骨气的行状。傅山用他的传神妙笔将头绪繁多的事件写得条理清晰,如细细勾勒出的一幅长长画卷,画出了在中国17世纪的一场政治斗争中,种种人物的表现和他们所处的政治生态环境。在揭示社会问题的同时也以热情的笔墨,歌颂了这场斗争中正直高尚、见义勇为的许多仁人志士。
在为袁继咸辩冤的整个过程中,傅山都是一个组织领导者和核心人物。但傅山却不为事后获得的义震天下的名声所累,而是在这篇文章中以“不敢粉饰一字,欺人要名一时”的态度,写出了这一事件最终获胜的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在真实地揭露时弊的同时,也不去夸大和自吹自己的功劳和作用。这种做人的谦逊和诚实的美德,让我们在读这篇文章时感受极深。
《汾二子传》是傅山先生传世的另一篇重要文章。这是傅山反抗暴政的代表作品。清顺治二年,南下的清军制造了“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这两桩让天下百姓没齿难忘的大惨案。顺治五年,也就是公元1648年,朝廷出于防止百姓造反的目的,又下了一道命令:禁止民间养马。在山西的北部和中部山区,老百姓世世代代以养马为生,不让养马,岂不断了他们的活路?矛盾是绝难调和的。于是盘踞在交山一带的农民军,首先向清廷军队发动进攻。紧接着,山西全省反抗清廷暴政的浪潮全面爆发。在强权与强暴面前从来也不肯屈服的傅山,便义无反顾地与汾阳薛宗周、王如金这两位在三立书院时的好友,一道投身到民间反暴政的斗争中去了。然而,这次遍及山西全省的武装大起义,却因为清廷摄政王多尔衮亲自率兵督师镇压,最后还是失败了。薛宗周和王如金这两位义士,在晋祠南堡与清军的巷战中魂断灵台。
事后傅山专为薛、王二人写了《汾二子传》。这篇文章分明触动着当权的统治者和他们的利益,为了不连累家人,傅山与兄弟分家另过,住进了土堂村里的净因寺。净因寺始建于北齐,位于崛山脚下,汾水岸边。寺外古柏参天,人称“土堂怪柏”,自古为太原一景;寺内有土洞,洞内有土佛,人称“土堂大佛”。在这尊土佛的注视下,傅山日复一日地抄写着《汾二子传》,让这些文字流入民间。他以这种不屈的文字,向世人表达了自己反对暴政的立场。
面对朱明王朝的腐败,傅山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以诗句直指朱氏皇族。对朱元璋的“龙子龙孙”们,他充满了始终抹不去的怨恨,用诗痛斥他们是“小松无数不成材,龙子龙孙尽麻蒿。”明亡后,傅山虽然出家做了道人,还在盂县的大山中作诗赞赏李自成旧部榆园军:“山中不诵无衣赋,遥伏黄寇拜义旗。”傅山不因这支队伍曾是前明王朝的叛逆而因事恶人,而是为他们敢于反抗清廷暴政的斗争所感动,甘愿“遥伏黄冠”去歌赞他们。傅山的许多诗歌和文章都是对时局有感而发,绝没有无病呻吟的无聊之作。当今那些远离现实,靠出卖隐私,以无聊手段自我炒作,借以浪得名声的所谓作家和诗人们,面对傅山的这些文章和诗歌,真应该如立于明镜之前,认真对照和反省一下自己。
贴近生活
文学的土壤永远离不开历史的积淀,这种土壤只能是文学家自己亲自参与的丰富现实生活。后人从傅山的诗歌中,可以看到先生故乡西村的风景民情,可以看到先生眼中的大好河山,还可以看到先生笔下同道义士们传神的各种精神风貌,和社会底层老百姓们的真实写照。清朝顺治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660年,傅山举家东迁,住到了太原东山脚下的松庄。那里当时有很多松树,村北是一片丘陵,村南是一条沙河滩。每当雨季来临的时候,洪水如猛兽一般从山上倾泻而下,滔滔河浪撼天动地,就像刚刚过去的那个时代,更像傅山心中曾经拥有过的壮烈情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康熙亲政后政治渐渐稳定,傅山开始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了社会的另一个层面,那就是生养了山西人民的这片沟壑纵横的黄土地,以及嵌在沟壑中的小村庄与生活在村庄里的那些老百姓。
一场春雪悄然而至,他会骑着小毛驴兴冲冲地走出家门,来到东山脚下的片片田畴旁观赏雪景。到了春播季节,傅山也会携儿带孙来到田间,全家人闻着泥土的芳香,瞅着犁浪在翻卷,耳畔听着“叮叮咚咚”的楼铃声。夏天到了,乡亲们也会把他围在树阴下,听这个大名鼎鼎的文人讲古论今。秋天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季节,他会与乡亲们笑谈收成,共话桑麻,运筹来年。傅山曾在松庄写下的一封书信中,真实地描述了自己与当地百姓融洽相处的生动画面:“姚大哥说,十九日请看唱,割肉二斤,烧饼煮茄,尽足受用。不知真个请不请,若到眼前无动静,便到红土沟吃碗大锅粥也好。”鲁迅先生曾在1927年写的日记附录《西牖出钞》中抄录了傅山的这封书信,指出傅山当时正是过着一种“萧散有味”的民间生活。
正是这种生活,使傅山始终不同于宫廷文人,在其诗赋文章中,从来没有沾染上一丝一毫的官本位习气。他的笔下,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学识,也有丰富多姿的民间宝藏。在傅山先生的诗歌和其他作品中,历史掌故和民俗民情常常被他糅于字里行间,从历史长河中随手拮取的宝藏,和从民间文化中着意挖掘的宝藏,都成了他创作中取之不尽的财富。我们以傅山存世的《红罗镜》、《齐人乞食》、《八仙庆寿》等为数不多的戏曲剧本为例,就可看到作者对晋阳地区民间风俗方言的借鉴和运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比如“爬不跌”、“跋躐”这些至今流传于民间的地方口语方言,在傅山的戏曲剧本中都可以找到。当我们今天认识到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一文学真理之后,重新体味和研究傅山的文学实践,就更具有独特的现实意义了。
笔下传神
太原民间关于傅山的各种传说中,涉及到先生书法和画技的故事不少。坐落于太原府西街的省政府在明清时期是山西的巡抚衙门,衙门对面有鼓楼,是明代建筑,太原解放后在城市改造中已经拆除。当年这座鼓楼上有几块名人写的牌匾,有一块牌匾上写的是“声闻四达”四个大字。相传这牌匾挂上鼓楼之时,才发现“达”字的坐车偏旁上少了一点。围观者议论,督造此事的官员一旁着急,正在此时,傅山先生来到。他当即让督造此事的官员备墨伺候,又让人找来一张弓一枝箭和一团棉花。傅山将棉花束于箭头上,再用其浸濡浓墨,弯弓搭箭,将其射向牌匾上的缺点“达”字。众人看时,只见那射出的箭已落地上,而原先缺点的“达”字已经完整了。
关于傅山的画,民间传说更多。相传太原有一位以卖豆腐为生的老汉,每天起早贪黑,却总是过着贫困的日子。傅山先生便画了一棵白菜送给他,并且嘱咐他说:有人来买这画时,你可千万不要贱卖了。老汉起初不以为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那颗白菜却越来越神奇——晴天看它时菜叶蔫蔫的像要枯死了,雨天看它却变得青翠欲滴,简直就是一颗活着的白菜。不用说,那幅“白菜图”卖了大价钱,据说是三百两银子。
还有一则传说,说的是太原一位有钱人,对傅山先生十分敬仰,屡屡向傅山求画而难得。傅山见其心诚,便对其说:“今年八月十五夜里,我可以为你作画一张,但到时还得看你我有无缘分。如果那天晚上没有月亮,这画我是断然画不出来了。”对方一听欣然不止,心想,八月十五晚上,岂能无月?到了八月十五,便早早将傅山请入家中后花园,先摆好酒宴,又设起书案摆上文房四宝,请傅山临场作画。但偏偏天上浓云密布,傅山让留下一名家人伺候,命主人与其他人全部离去。然后,傅山便边饮酒边作画。饮酒到微醉时,提笔泼墨,在纸上挥洒自如,浓墨淋漓,傅山本人也手舞足蹈,整个身体如癫似狂了。那名奉命伺候傅山作画的家人不知究里,以为傅山酒醉欲倒,急忙上前一把抱住了傅山。傅山的画兴被无辜打断,掷笔于地,叹道:“你败了我的画兴,这画是画不成了。”说毕,不辞而去。待那家主人闻讯来到后花园时,只见书案上宣纸洁白,上面一团浓墨,并未再画出其他形状。因是傅山遗稿便不忍心扔掉,小心放回书房,展在书案上想再请傅山先生完稿。不料这纸上的那一团浓墨中突然透出银光,竟照亮了整个书房。细看时,原来那一团浓墨分明是一团浓云,隐藏在这团浓云中的一轮明月,正在走出云团吐出一团光华。
任何民间传说,都附载着来自民间的情感和理想,并非空穴来风。傅山的书画艺术,其水准和境界,越到晚年越是炉火纯青的高妙境界,取得了卓尔不凡的成就。
书法真谛
傅山先生的书法主张是“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说白了就是“大巧若拙,形神兼备”。这也可以称为傅山书法的纲领,和他的书法所以能达到巅峰的真谛。
著名书法家林鹏认为:一个艺术家,进行了广泛的艺术实践和深入的艺术探索,他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理论。这些理论,就其本质来说都是他们的心得体会……傅山在书法艺术上提出的“四宁四毋”的审美原则和创作原则,其影响之深远是众所周知的。
字如其人,傅山的书法艺术风格,表现了他光明峻洁的高尚人格和博大宏深的学识修养。他的大楷正而不拘,庄而不隆。小楷笔法清劲,布局和谐,点画之间多有意趣。隶书古劲刚健,拙朴有神。傅山传世的书法作品中,尤其以行草见长,这类作品中的精品甚多,有的一气呵成、刚健洒脱,有的忽行忽草、神采焕发。他的草书《五峰山草书碑》就堪称草书艺术的典范,笔下龙腾虎跃,蛇行草伏,气韵连贯,磅礴夺人。
傅山的书法作品《西村漫吟》,是他晚年的一幅作品,原作系12条屏,共书写36行,计373个字。我们在太原汾河东畔的傅山碑林公园内,可以看到由当代人根据原作勒于石碑之上的这幅作品,作品尾处自书“七十四岁老人傅山书”。
书法界人士指出,《西村漫吟》“是一篇耐人寻味的书法美学诗章”。因为在这幅书法作品中,傅山的诗文是立足故乡西村的景色,转而说到了书法技艺,在评介和论说书法技艺时,又反复地批判奴性。比如“鹜书有何好,此谬由诸君”这句,何为鹜?鹜即野鸦子;何为鹜书?也就是将野鸭子相对于家鸡而言。野鸭子虽然笨拙,但它是自由自在的。而家鸡呢?虽然它们的行为乖巧也讨人喜欢,更不缺食物,但它们却是依附于主人而失却了自由的一种生命,书法的生命与人的生命是一样的,没有自由而唯有依附于别的成功者,那实在没有新路,也没有出息。这种书艺认识,与傅山以前的“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的书法真谛相辅相成。再如“作字见无字,制心闻不闻”一句,从哲学的角度讲,这种书法理论就是要让书法者从必然王国向着自由王国挺进,从而达到出神入化、随心所欲的艺术境界。书法艺术是有规矩的,这便是“古法”,也即今天所说的传统。失却了传统便失去了根,这不可取。同理,一味拘泥于传统,则会少了变革和进步,也不可取。傅山说“法本无法”,写书法时不能用前人写的字遮住双眼,此即“作字见无字”;想到和体会出书法艺术的传统技法时,决不可又被这规矩约束了手中的笔,这就要做到“制心闻不闻”了。
晚年的傅山,其艺术灵魂已伴随着生命的超脱潇洒而变得更加含蓄和深沉。傅山先生的最后一幅书法作品,是他在78岁时写出的巨幅长卷《晋公千古一快帖》。那雄厚苍劲的笔锋,至今依然让所有的观赏者感动。郭沫若在《跋〈晋公千古一快帖〉》中这样评价傅山的书法:“傅青主豪迈不羁,脱略蹊径。晚岁作此,真可谓志在千里。”
清初第一
傅山的绘画作品虽然比书法作品流传下来的要少一些,但其艺术价值却可以与书法相媲美。据一些史料记载,傅山年轻时就对书画有了极深的研究。太原城内有一位姓黄的举人,因为祖上曾在晋王府里做过官,所以传下来一批历代名人字画。若论功名,傅山当时还只是一名廪生,却被这位举人待为上客,常常把他请去甄别字画,鉴赏书法,或许,还要纵论古今呢。由此可见,青年傅山已经是太原有名望的书画界名人了。
傅山的写意画大多粗犷萧疏,正是他自己精神和人格的写照。艺术上勇于开拓的革新精神,又与他的人生理想与人格魅力相一致。论书法,傅山的“真、草、隶、篆、行、楷”样样精通;论绘画,或山峦瀑布,或松柏梅竹,都借景抒情,处处表现出自己的风骨。难怪清代一些文人推崇他为“晋唐以下第一家”,说他的“书法绘画,皆绝古今,世人咸知宝贵。”书画大家郑板桥与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就是傅山书法的崇拜者。
松庄的四周有许多松树,苍松傲骨恰恰是傅山的性格,所以,他特别喜爱画松。康熙二年是傅山侨居松庄的第四个年头。这一年,他接待了来自江苏昆山的顾炎武。顾炎武比傅山小7岁,之所以跋山涉水来到太原,来到东山脚下的这间土窑洞里,是因为久仰傅山的名节和学问。两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同年,顾炎武又访傅山,两人切磋学问,相互赠诗唱和。顾炎武在和诗中对傅山赞道:“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表达了对傅山人格学问的崇敬。康熙十五年九月阎尔梅来访,傅山挥毫泼墨,画了一幅《岁寒古松图》相赠。傅山被同一时代的大家名士比作“老树”,他又画“古松”赠与同一时代的另一位大家名士,傅山自己不就是一棵饱经风雨历久弥坚,而艺术生命长青的不老苍松吗?
傅山的绘画作品大多粗犷萧疏,其代表作有《丘壑磊》、《天泉舞柏》、《寒谷松杉》、《风竹》等。在《丘壑磊》的画境中,冈峦起伏,远峰鳞次,红枫倒垂,老柏傲立,崖壁无欲,刚强自立。《风竹》更有特点,在长幅窄条上画了一竿高竹直冲天际,显现出顶天立地、宁折不弯之志。
傅山的书画作品不仅仅在于艺术上的造诣,更值得推崇的是他不入流俗、勇于开拓的革新精神。而这种精神,又与他的人生理想与人格魅力相一致。说傅山是中国历史上的书画奇人,其书画艺术是清初第一,当之无愧。
文学大师书画奇人傅山 |
最新资讯更多
资讯推荐更多
资讯热点更多
联系信息兜底儿网艺术交流专家服务中心(巡天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