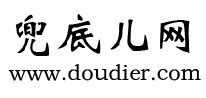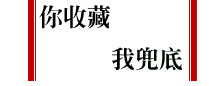哲人说,人生就是一场磨难。忧愁与困苦,挫折与痛苦,终将相伴终生。度过了一个磨难,新的磨难又接踵而至。这是我们必须要承受的生活的压力,因此我们不要害怕它。
这是一种达观的观点,人生是场磨难,在困难的隙缝中游刃,有助于激发志者的勇气,磨练其心志,重要的是向磨难挥剑的过程中,精神上获得净化、重组和愉悦,丰富人生的蕴涵。所以,在生活中被煮过的人,有的人成为精英,有的人成为草芥。
又是一个火热的夏天, 1966年的夏天,加头河岸上茂盛的杨树、柳树成阴,许多人在大树底下摇着蒲扇乘凉,那架古老的小桥横在浅浅的水中央,浓密的树阴里传出阵阵撩人的知了的叫声。对张清智来说本该是人生中又一个转折。今年他从从吴村小学六年级毕业,全班40个人,经过考试,只有8个考上了尚岩中学。张清智是其中之一,并且成绩名列前茅。
张清智早就向往那所中学了。两年前,因为哥哥好长时间没有回家了,母亲挂念的厉害,就带着清智去他找大哥。张清智第一次走进青砖垒成的瓦房,看到教室里整齐的座位,整齐的课本摞在桌子上,看着一个个同学读着高贵的外语,站在操场上他呼吸着学习的气息,他心旷神怡。他在心里暗暗发狠将来一定要考上尚岩中学。所以,打那以后,尽管他平时画画占用时间,但他仍坚持学好文化课。
父亲很激动,在大儿子1964年年考上了西安民族学院后,家里有望再出一个大学生了。大学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将来的不用再一个汗珠子摔八瓣,可以有稳定的生活和日子。走出农村的唯一的途径就是上大学。
父亲听到消息的当天,从垛的麦秸中拨拉了一整天,捡出了一堆粗实、净亮的秸杆。在门口用四个木棍支起了个架子,用砖头栓上线,打起了苫子。
草苫子是农村床上最好的糅子,那时候棉花的床垫是一件极为奢侈的用品,农村人整年铺在身下的就是草苫子。
父亲打这床苫子下了不少工夫,不仅比平常单人床的苫子宽,而且在苫子的边上还给做做成整齐的秸花,父亲为的是让清智能在学校众多的同学面前不丢脸。这种苫子很少铺,通常是给新娶的小媳妇做的铺盖。新媳妇享有至高的权利。
父亲穿花引蝶打了两天,在火热的天气中站了整整两天。他消瘦的脸上溢满笑容,他给去外地上学的儿子打的苫子,不仅样式好看,而且厚薄均匀,麦秸整齐划一,毫无瑕疵。
苫子打完了,父亲为防止它受潮,把它放在屋子里,用隔版高高把它垫起来。
还有两天就要上学的哪天早晨,村里的喇叭里播出了一个通知,所有毕业的学生全回六年级再上一年,尚岩中学停止教学活动。清智那时候正躺在床上,听到广播满肚子委屈,父亲唉声叹气,抽一口烟对清智的母亲说:“又乱了!”许多和清智同样的孩子怏怏地接受了又回去上学的通知,也有一些孩子主动退了学。清智默默将苫子收好放在床上,开学的时候,他又回了六年级。老师告诉他,上面已经乱套了。接着当地的中学停止了所有的教学活动,学生们回家的回家,整天在外面玩闹的玩闹,学校名存实亡。在张清智所上的老六年级,转眼间竟也如鸟兽散了。他们是受伐害的一代。
生命本质艰难,面对这种艰难,要想成为人上人,必须能抗拒这种艰难对生命的撞击,必须吃得苦中苦。“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是人生的至理训教。
张清智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像扔下晦气似的扔掉书本捡起锄头。他拿起锄头的同时也拿着书和笔。他想,学上不成了,我要用画笔塑造冲破寰宇的火箭。
在田埂上,他对着舒叶含须的玉米;在河畔,他看着岸上松柏后面那若隐若现的小石屋;在门口,他注视着下地赶回来的骡子和驴;在路上,他观察扛着锄头的老农;在家里,他观察母亲拉着风箱做饭的动作;在晚上,他在如豆的煤油灯下勾勒;在梦中,他不停地晃动握笔姿势的右手,速写的形象在脑海中一个接一个地浮起……
灵犀一点是吾师,功夫不负有心人,张清智的绘画基础一天比一天牢固。疑想形物,搜妙创真,通过对大自然细致的观察,对生活中草木花鸟的揣摩,他在当时简单的纸张上创造出了许多富有概括力的形神兼备的艺术形象。
县里有个放映队,常常下乡到各个村寨里去放一些无产阶级的短片、幻灯片。宣传队里的口号是革命教育不能放松必须天天抓,而承担着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的放映队手头上放来放去却还是那几个短片。放映队里有个绰号叫猴子嘴的知道张清智画画好,就骑车找到张清智让他给画一些画,专门给张清智留下了一堆创作用的透明的玻璃纸。接到任务,张清智心里既紧张又高兴。这对于刚要上初中的他来说是个百斤的糖蛋,沉重且甜蜜。他挑选以前创作的作品细致地加以修改又拷贝到玻璃纸上。几天后,县放映队在加头村放映了一组颇有新意的幻灯片,受到群众的热烈好评,然而谁都没有想到这是出自张清智之手。后来这组幻灯在全县巡回放映,很受社员们的欢迎。
在芸芸众生中,张清智脱颖而出。
张清智大地之梦:重返六年级 |
最新资讯更多
资讯推荐更多
资讯热点更多
联系信息兜底儿网艺术交流专家服务中心(巡天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