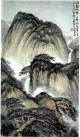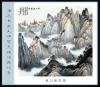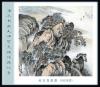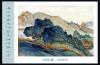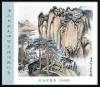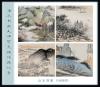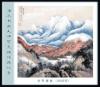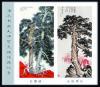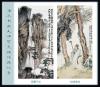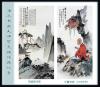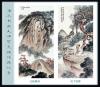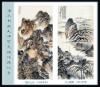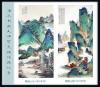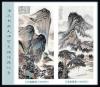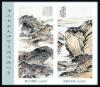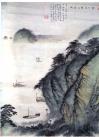润祥鉴赏:中国画派与名家欣赏 373 (海上画派 贺天健 10)
贺天健曾自言:“在我六七十年的生活中,在艺能上起着大变特变的感情的,要算这一阶段的十年里了。”
从新中国成立前后直至“文革”初画家75岁这一段时期,是画家创作的鼎盛期。他保持充沛的变革与探索热情,以丰富多样的作品相继在丹麦、北京美术展览馆、上海美术展览馆举办了多次大型个人画展。即便到了“文革”后期,画家耄耋之年为数不多的创作中,我们仍可从中捕捉到其一贯创意求变的浓烈气息。
“笔墨当随时代”,这句话是傅抱石当年借石涛语对贺天健山水画展作评介时的文题,既是赞语,也是那一时期像傅抱石、贺天健等从传统中求创新的一批中国画家的心得感怀。
我们知道,建国后的中国画创作一直备受甚嚣尘上的“笔墨虚无论”影响。1954年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的画展上,美术史家王逊即质疑笔墨作为评判艺术的至上标准,主张以“科学的写实技术”、“为今后的国画服务”的观点。无疑,他的声音代表了当时声势浩大的以西画改良中国画派的普遍想法。虽然此话一出,便遭到当时国粹派第二代秦仲文等人的坚决反对。一方面,在建国后如火如荼的国画改造运动中,被覆在“保守主义”的不韪阴影之下,不少画家纷纷采取退让和折中的办法,从旧式的文人画形制中谋求作风的丕变。他们在向“写生山水”作过渡型努力时,却极可惜地舍弃了文人画传统中许多精髓的元素,而大量掺入西画式的图模写真法。相形之下,同样作为传统中走过来的画家,贺天健在新历史背景下虽然也响应运动号召,积极作中国画的改良与创新探索,但在对传统的维护和继承方面,他对于扬弃之道始终具有超越他人的清醒体察。贺天健晚年陆续撰写并发表了数十万字的理论文章与著作,多有对传统与创新问题的申述,以及如何区别传统画学中的良莠、“可学”与“不可学”的鉴别。这里他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观点,是主张向传统中具有发展机能的流派去学习。他说:“向好的传统学习,而且认清传统的‘动的机能条件’,学习就不会僵化。”“学古而化”,能大胆创新;惧“古”而图“化”,只能是无知者无畏,谋取惊奇而已。现在看来,在当时的大局环境下,在全国风起云涌的“艺术大众化”和“国画西画化”的浪潮中,这种严肃的呼吁不乏矫正视听的深刻意义。同样在他于20世纪60年代主持上海中国画院工作时,先后收邱陶峰、苗重安为关门弟子,仍坚持以传统的导师课徒制授学,最强调临摹的重要,让弟子依循师传统与师造化并进、野外写生与创稿兼习的实践道路。其课业除了山水花鸟各科,还包括画史画论、书法、诗赋等,皆是画院内各擅胜场的老画师们担任主讲人。这一极富文人画特色的教学模式,对维护中国画传统在继往开来的发展道路中能薪火传递,一脉相承,无疑是功不可没的。尤在当时国画学科建设中,苏派写生风靡的“一边倒”形势下,实属凤毛麟角,难能可贵。作为建国后海上山水画家中贡献突出的一位,贺天健对于海上画坛能继“民国”,在建国后相当长时间继续保持焕然全备、形式风格稳健鲜活的创造态势,并以精进的学术研究标领于全国,应该说不无重要的作用。
在这种艺术观的带动下,贺天健该阶段的绘画创作完成了他毕生最重要的变革与升华,最终奠定了他在现代画史上的地位与价值。我们不妨称之为“现实主义的新式文人画”。
这一时期画家尤其注重两个方面。一是借助西画原理与古法的“迁想妙得”,从构图和色彩上帮助国画拓展意境的表现。二是重视现实取材中提纲挈领,把握对象的精神。所以,贺天健对生活素材的运用,始终是视之为表现的手段,而不是创作的终极目的。
画家此时的代表作《惠农晨曦》、《渔家乐》、《插秧图》、《大戈壁远景颂》、《梅山水库之西北》、《漕运图》等,开始将探索重点放在现代人物的配景山水画方面。其间他多次前往上海近郊参观访问,到安徽合肥的佛子岭水库、梅山水库以及巢湖、桐江、黄山等地采风写生。十余年来他还一直坚持作人物速写,练习不辍,并且尝试创作现实生活中的现代着装人物与各种劳动场景。这时,画家不仅改画现代人物了,连山水创作,也多有劳动场面的时代感氛围。
内容决定形式。从这类新视角的取材中,画家找到了风格创新的契机。从逐一产生的技法的矛盾而逐一寻求解决,从逐步的局面的变革而寻求整体的彻底的实变。所以,无论从贺天健的笔墨、形式语言各方面看,画家这类新事物、新气象的题材创作,具有谐调、酣畅的统一感,没有同时期很多画家在探索中西、古今结合时种种捉襟见肘的不适。他提倡国画创作中要加强提高透视与色彩学的应用,但并不是在现实题材中生硬套用这两种科学方法,而是同时也注重如何在意境和布局中,运用艺术的想象力来变易实境,使画面更为美观。
另一则是青绿技法的突破与自创。贺天健的青绿山水是他中年以后精研的独擅绝技。他以明代的精制茧纸、乾隆时的高丽名笺和明代的石青石绿为画材,用独创的方法自行研磨;并且在画技上,也通过研读古代画史画传,琢磨出一套独特的“螺青法”和“笼青法”。他晚年对于青绿山水法的突破,则更体现在借鉴西洋画法的施色,赋予中国画以更为浓重饱满的色调、更为生动的气息氛围,破除了自古以来青绿、金碧山水作为一种堂皇威严的庙堂院体画,一贯精工典丽、整饬繁复的呆板格式。贺天健的青绿创格,在于他融会了画家的多种笔意技法,兼具浅绛的笔墨滋润与青绿的明艳,又比以往任何青绿或金碧山水更为恣放,富于写意的灵异韵味、写生的生动气息。打个比方,如果说他中年以前的青绿山水变法是一变浓妆为淡抹,则他晚年的青绿变法是再变淡抹为浓妆,却依然保持画中生动扑面的清新格调,富含灵活流动的气机。
对于贺天健这种青绿山水格式,在当时老派的业内人看来是“非正宗”,也有人指为“新派画”。但画家本人对这样的议论反以为慰。他自中年以来便一直提倡国画的再发展,对于时代这样的大变革,认为除了内容,国画的风格更应该革新,不应该停留在“现象的浮变”上。对于他在国画本质上的这种探索精神,当年的同道好友黄宾虹、傅抱石都纷纷给予肯定和支持。1952年在贺天健成功创作了巨幅金碧山水《锦绣河山》后,黄宾虹闻讯即手书道贺,赞此“新创”将“光大美术”。
贺天健注重生活与创作的联系,注重写生造化的现实主义创作观,在建国后蓬勃昂扬的社会大环境中得到了合宜的文化气候,得以成就了他本人从文人画而来的革新与再创造。虽然在当时,包括像吴湖帆等文人画家都在积极汲取变革中国画的因子,但真正达到圆融完熟境界者并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