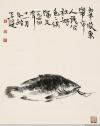润祥鉴赏:中国画派与名家欣赏 371 (海上画派 贺天健 8)
贺天健毕生绘画治学态度严谨,阶段性的画风嬗变线索明晰。结合其艺术经历概略可分为:一、临摹写生阶段(少年-37岁左右);二、风格自创、向外发展阶段(37-57岁左右);三、变革阶段(57-70岁左右)。
临摹写生阶段 (少年-37岁左右)
贺天健属于自学型画家。他从界画式严谨的临习默写训练入门,同时从邻人旧藏的吴门派山水画卷册那里,开始爱上“画中山”,获得了临摹山水的最初启蒙。以“游学”、“偷学”的方式,从明至清,从吴派沈周、文徵明,到曾经的朝廷供奉、本乡画家华冠乃至王时敏、王石谷等,无不涉习。他自少年时独对吴门派的沈、文作品一见倾心,或许只是本能地受到吸引,对画中这片熟悉的三湖九泖风光感到亲切。而稍了解画史者都知道,这两位吴派的发创者是传赵孟頫、元四家之笔的,他们重视以笔致墨韵传达画境情趣,重视写生造化,往往是 “图写真景以记”,以此启悟灵机,而非专于一家习气处。这样的启蒙对于像贺天健这样的初学者来说,如同学画先从正道登堂入室,而绝少沾染偏门习气。就笔性墨性的最初培养上讲,凭此一点,就远远胜过同时代那些从“后小四王”的末流画风入手为学的画家了。
在贺天健的临摹写生阶段,他并不单纯求学于“画中山水”。自开始他即明白一个重要道理:真山水其实是画中山的蓝本,对于画中山须探本求源。他又从不少明末清初画作上的“仿某某笔”、“拟某某意”中获得反面的批评,明白了独立创稿的重要,开始追溯到宋、元那些开创家派的画家那里去学习。荆浩、巨然、郭熙、黄公望这些大家的作品没法看到,就从他们留下的画史画论中按图索骥地师法自然。他也常常蹈习古人范宽、黄公望的作风,借助少时写真练就的目力和观察力,游历家乡附近的山水,体验会心;从奇山异石中求证画中的山水来由,探求真山水和画中山水的差异。
写生、创稿,到大自然中去体会、质证画中山水,同时将临摹当成了写生的张本和写生的工具。这彼此之间的相与相成,促使贺天健走上了一条与画学陈规不同的、以师造化与师古法相参的绘画创作之路。这令他的山水画创作能别具一番浓厚的生机,别有一种清新鲜活的画品气息。而这恰恰是其他一些单纯从师法古人中取径,进而再奋力摆脱窠臼、自化一格的传统派画家所难及的。
贺天健在临摹写生阶段的另一可贵之处,是他“兼爱并学”的实践。傅抱石曾评贺天健:“从他所处的环境所经的途径研究,我觉得却很少‘四王’的影响……他是应该有便利那么做的。”说少受“四王”影响,并非说明贺对“四王”接触不多、临摹不多,相反,贺天健中年以前,受当时的海上画坛影响,对“四王”浸习颇深。毕竟当时上海仍以吴穀祥、杨伯润这样接“四王”余绪的画家势力占上风,这样的影响力对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来讲,是难以抵抗的。而在贺天健眼里,“四王”代表的是一种文人画的画理规律。他把这类画称为“界画”,意指它们有严谨的规范法度,对于后学者循序渐进地理解画学理法的支脉源流,是有切实的功效的。贺天健之学传统,有着和黄宾虹一样穷究极研的精神,主张对于各家笔墨,要苦心孤诣地下硬功夫、死功夫,要背默如流,烂熟于胸而能信笔拈来,这样才能丰富自己的学识储藏,是为学的第一步。他说学传统、学本领“要从死里边活过来”。而能避免因之而“结壳”,便得益于他自少年起开始的“兼爱并学”,也即是把界画和法画(清初“四僧”和清中期“扬州八怪”一路疏体写意画的总称)相参互学的过程。这使他能够在两种不同旨趣的比勘中,辩证地各取所长,不会盲目地从学。更关键的,是避免了因“过熟”而生习气。所以,贺天健学“法家山水”,更注重参学他们在自然中捕捉神韵、以臻化境的艺术体验法,以流动的自然观照、不断的新鲜刺激充实心源。这种鲜活的感性认识能够及时纠正对规律性理法钻研过久后导致的刻板与陈陈相因的“老面孔”,帮助画家及时摆脱习气,在熟境以外另行开拓。
贺天健这种“兼爱并学”,表现为对于西画也并不排斥。西画的直面写生,更成为他大胆向自然索要画材的助力;而西洋绘画的色彩法、色调感的处理,也微妙地影响了贺天健日后墨彩画的构思经营与布局施色。
如果说,贺天健早期的绘画实践取的是“法画”和“界画”兼爱并学的横向发展,那么,自二十六七岁之后的十年左右,贺天健更重视对笔墨技法条分缕析、追流溯源的纵向求索。不仅能对古人各家各派的风格面貌,了悟其精神,掌握其技法演变的关键;而且开始对于阔笔、细笔画,各从笔性、笔势上具体而微地研究练习。此时的贺天健已开始作八尺以上的大幅画,由经验中得出创作的关键是要找到整笔和散笔两者间的分歧点:作大画宜整笔,得格局开张、气机酣畅、骨架气魄昂藏结实;六尺以内、一尺以上的小画则宜散笔,除非如南宋小品画那样重章法和笔法,否则若以阔笔写来,会缺少耐看的精微韵致。这一收获使得贺天健在日后创作中能做到收放自如,尤其大画,独具海派其他独擅散笔的山水画家所没有的伟岸气格。
从其该阶段代表作《仿黄鹤山樵写秋山行云图》、《写意山水册》、《空谷佳人》等可见,这一时期的贺天健,业已开始对画品、情性的表达多加探讨和思索。对于清代以来画品权威对江湖、山林、市井、庙堂、书卷五种气息高下的评断,也得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在他看来,山林和书卷气的画是偏重于散笔阔笔的松疏逸放,有姿致但放松了对物象的真实要求,也就是缺乏自然山水的鲜活气息,这是造成大小“四王”面貌的根源。而这种写真山水的情境,反而在五代、宋名迹的山水草木中蕴含着。江湖气和市井气是负贩陈陈相因的旧画稿,无格无韵,是江湖上的低级画派。庙堂气以“四王”最为擅长,这种士大夫的贵族华章也是最不易学到的。画家对这五种画格标准的品藻,旨在扬弃地汲取,而非单纯地依附,这对成就他本人创作多样化的美学面貌,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理论支持。